2015年,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副驾驶员Andreas Lubitz驾驶9525航班撞山,机上所有人员遇难,这一悲剧让飞行员的心理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对这次坠机事件的直接回应,所有欧洲的航空公司必须在2020年8月之前为机组人员准备好心理健康支持计划,但飞行员们愿意寻求这样的帮助吗?

“到2020年,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有所准备,”英国航空心理学中心的临床与航空心理学专家Rob. Bor.说到。“无论他们是购买国家为飞行员打造的解决方案,还是采用自己完成的独有的版本,到那时,他们都需要接受。”
这些方案的目的是帮助飞行员识别、应对和克服那些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安全操作能力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在城里工作,把办公桌搞的一团糟,没有人会死。”Allaxa的管理顾问,特许心理学专家Marc Atherton说到。“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即便是一个很短暂的失误,也能够很快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额外的压力现在被业界认为是值得积极应对的。在文化层面上,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变化。”
Atherton先生说道,在任何时候,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都在与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做斗争。“我们绝对没有理由来假设飞行员不在这一统计数据之列。”
同侪互助
飞行员是在高压的环境下工作,还要跨越不同的时区,工作不规律,经常和看不见的陌生人在一起,和他们的经理以及家庭这些支撑他们的网络是完全分离的。这种生活状态也会给人际关系带来巨大的压力,而通常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
“对于飞行员来说,可能有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就是他们都像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飞行员那样,不屈服于压力,”欧洲同侪互助倡议组织(EPPSI)主席Paul Reuter说到。“从专业的角度,我们需要认识到,飞行员并非个个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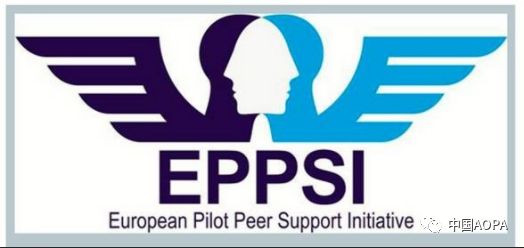
EPPSI关注的是同侪互助网络和同侪互帮项目的建设上,在这些项目中,来自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志愿者被训练以一种同情和不带评判的方式倾听他们同事的问题所在,而且要确保秘密。
和有着一手工作经验的同事交谈,不像寻求正式的医疗帮助那么可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志愿者都是由合格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监督,并提供指导的,如果情况变得过于复杂,专业人士可以立马接手。
要想有效,同侪互助网络就需要得到航空公司的管理层的支持,但不能由他们来进行管理,否则保密性和有效性就会打折扣。
“如果员工不信任这个组织,他们就不会站出来说“我觉得无法胜任这项任务”。”Reuter说到。
来自工会的支持也是很有帮助的,但要把同侪互助组织和其他劳工问题区分开来。Reuter警告:“不要把他们混同在一起。”
保密原则带来了复杂性。航空公司或监管机构如何监管涉密项目?什么统计数据可以报告?监督机构和许可机构在什么阶段可以介入?
“这些事情你必须考虑,要保持开放,并展开对话,”Reuter说到。“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透明、一致认同的流程,把每个人都正规的记录下来。可以这么讲,我认为同侪互助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次对信任的升华。同侪互助不是基于规则,而是基于伙伴间的关系。如果你想让它发挥作用,相互的信任和透明度是关键因素。”
基于这一点,EPPSI计划在2019年底前发布一些同侪互助的最佳实践指南。“希望这是一个鲜活的文件,这样我们就能用共同的知识来源,为那些想要建立同侪互助网络的组织提供支持。”
这种心理健康急救对航空业来说并不新鲜。在1991年,澳大利亚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和澳航就建立了一个早期的航空同侪互助网络,成为该领域的领先者。德国的慈善组织飞行员呼救基金会在1994年紧随其后,为德国各地,来自任何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提供帮助。该基金会的想法就是如果飞行员打了求援的电话,他们就需要立刻获得帮助。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坠机事件发生后,飞行员呼救基金会在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支撑下,向德国之翼的9个基地派驻了飞行员的同事来进行同侪互助,这让这个基金会的知名度进一步得到提高。该基金会目前有200名志愿者,每年能帮助600~800个机组同事,并且帮助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南非和美国建立了同侪互助网络。
类似的计划还有包括美国的“银翼超人计划”(成立于2011年)、新西兰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的同侪互助网络和英航的“极速鸟”(2017年建立)。
飞行员呼救基金会的创立者,既是飞行员也是航空心理学专家的Gerhard Fahnenbruck先生说到,同侪互助项目也有着良好的商业价值。

最佳实践
专家建议遵循以下的原则来为飞行员创建一个有效的同侪互助网络:
• 确保这项服务独立于航空公司。
• 提供的支持必须不是为了处罚谁,且容易对接,无需等待。
• 保密服务是建立互信的基础,为飞行员创建一个安全的空间,因为他们是脆弱的群体。
• 程序要有良好的结构和透明度。
• 合作是关键,工会的介入有助于飞行员的参与。
• 确保人们知道有这类服务,以及这类服务包含什么内容。
• 和志愿者们一起来甄别他们的动机何在。
• 要为志愿者们提供正规的培训(这通常算作出勤)。
• 志愿者们必须能够获得训练有素的心理健康专家的精神上的支持和监督。

在正常情况下,飞行员们自己联系这类服务。一名志愿者会听取飞行员遇到的问题,并在需要进一步帮助时,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服务指导。“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能理解我听到的问题,”Long说到。
负责监督的心理学专家也在保密范围之内,他们给这些志愿者提供意见指导,供这些志愿者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正确。这些完全独立于航空公司管理层之外。
“我们讲保密意味着什么,这是获得飞行员支持最重要的事情。”他补充道。
志愿者们通常会获得诸如花名册更改之类的一些简要的通告。这样在不泄露秘密的情况下,志愿者们可以鼓励飞行员们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
“问题是,若他们不想和医生交谈,他们会和谁交谈呢?答案是和同行。”英国民航局(CAA)主管飞行员同侪互助网络的Nick Goodwyn说到。
然而,心理健康的变糟是缓慢和微妙的,所以飞行员自身可能还意识不到他们有了问题。
“靠飞行员的自我觉醒是很困难的,”共生公司总经理兼首席职业心理学专家Karen Moore说到。“那些了解你,但又不经常见到你的人,是最能发现你心理上微小变化的。”
当事人的同事或者家人可以联系提供保密服务的“极速鸟”组织。他们可以获得如何鼓励当事人去寻求帮助的指导。如果这不起作用,而且“极速鸟”组织中负责监督的心理学专家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要对此提起关注, 则“极速鸟”的一名同侪志愿者就会直接和机组成员接触。如果当事人仍然不愿意配合,且存在有可能危机飞行安全的情况时,心理学专家就可能会参与进来,与机组接触进行更高层次的干预。
“这不能是一个陷阱门,一份报告就把他们从花名册上抹掉。这个方案必须有几个不断升级的阶段组成,”英航的Fielding机长说到。“我们需要这些方案。千真万确,我们需要这些方案。那些说“我们的飞行员很正常,他们没有问题”的航空公司,都是在撒谎。”
“这项工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揭开这类服务的神秘面纱,为其正名,”他说到。“如果这类服务被认为是航空公司的工具,这些马儿就会跑掉的,他们不会参与进来。”

肖治垣(Robert Xiao),中国AOPA副理事长,中国民用航空网航家。
作者介绍



